重新思考西方、重新思考当代艺术
安尼施·卡普尔个展于2019年10月26日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。安尼施·卡普尔毫无疑问是当今最负盛名的当代艺术家,也是拥有最多的国际艺术资源、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。但是在今天,在历史产生巨大变革的时期,我们能不能对当代艺术重新进行判断,重新思考,建立新的批判性视野和新的思维框架。安尼施·卡普尔的文化价值究竟在哪里?
1968年第一届日本现代户外雕塑展,26岁的日本艺术家关根伸夫在一座公园内挖出一个深2.7米、直径2.2米的圆坑,而挖出的泥土被放置地面塑造成与圆坑大小一样的圆柱体。这件作品《位相——大地》是日本“物派”艺术运动的开端和象征,它利用了自然环境中的正负形体作为艺术表现手法。这和安尼施·卡普尔的作品《尖顶与深坑》在方法上异曲同工(时间更早)。
1968年日本经济超过西德称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经济上的成功导致日本艺术家更主动思考自身的文化特性,希望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找到自身独特的文化属性,摆脱二战后在美国主导的消费文化对全球文化形成的覆盖。关根申夫关心真正的文化问题,他的作品有着本能的文化反应,也有着惊为天人的表现力和生命冲动,是日本当代艺术家,甚至是亚洲文化自我意识的一次觉醒。与之相比,安尼施·卡普尔的《尖顶与深坑》更多是一种新奇的体验。它精致、有趣、漂亮、纤巧,却没有更多的文化意味。安尼施·卡普尔,他的问题意识在哪里?
2019年5月15日,在佳士得纽约战后及当代艺术晚间拍卖上,杰夫·昆斯作于1986年的不锈钢雕塑作品《兔子》,以910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,刷新在世艺术家作品拍卖纪录。这也使昆斯成为全世界最贵的在世艺术家。
这是后现代主义艺术的胜利么?不,这恰恰意味着后现代主义的衰落。这件天价艺术作品在世界各大艺术博物馆中展出,占据了世界上主要的文化资源,吸引着世界媒体的注意,除了一个空洞的金融数字,再无其它文化内涵。艺术,完全成为金钱的符号。这是文化的危机,而不是“胜利”。
2012年美国当代艺术家杰夫·昆斯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了一场讲座,介绍了他“1978年以来的艺术创作”,当时在整个中央美术学院“盛况空前”。这个把“当代艺术像商品一样生产”的艺术家,其“艺术成功学”的观点在中央美术学院具有很难来想象的吸引力,整个美院表现得近乎狂热。我们有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些艺术家的文化价值?我们到底从西方文化中学到了什么?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?我们善于模仿,却缺乏独立思考。一味的迎合恰恰意味着中国当代艺术思想上的不成熟。缺乏对时代的敏感和问题意识,才是我们真正的问题。
为什么杰夫·昆斯的“兔子”这样的艺术,明明没有一点文化价值,却获得全世界最重要的博物馆、美术馆、艺术批评、拍卖会、艺术市场、艺术院校及整个全球艺术体系的支持?
在《印象派的敌人》一书中,与莫奈同一时期的艺术家中,售价最高的艺术家是梅索尼埃,他也是当时社会上最知名的艺术家。在1890年,他的作品《1814,法兰西之役》以85万法郎成交,这是当时在世画家的最高价格。而当时提奥(梵高弟弟)提供给梵高的一个月生活费(包括画材费)才100法郎,可见当时艺术作品就已达到了很难来想象的价格。而时至今日,莫奈早已名垂青史,而世界上还有几人知道梅索尼埃?历史证明,权力、地位、金钱、名望都不是判断文化价值的根本因素。艺术,说到底仍然是一种精神产品,它取决于艺术家的真挚、热忱、对时代的敏锐和判断、个人的创造力和勇敢。
喜欢制造震惊效果的达明·赫斯特(过于聪明,擅长制造令人震惊效果的艺术家)
班克斯的《气球女孩》在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上刚以104.2万英镑成交,隐藏在内的碎纸机应时而动,将画作碎成条状。此举被认为是班克斯本人按下遥控开启碎纸机,故弄玄虚,有意炒作
达明·赫斯特、村上隆、杰夫·昆斯、班克斯、埃利亚松、安尼施·卡普尔、草间弥斯、蔡国强,上述的明星艺术家善于迎合市场,但缺乏对时代的敏感和认知的深度。他们擅长于制作炫目的效果,新奇的感受和漂亮的装饰,但是艺术史并不是以此为判断依据。在今天这些世界最知名的艺术家,动不动制作一件作品的制作成本就高达数百万、上千万的资本,我真得很疑惑:没有巨额资本的支持,艺术家就做不出好作品了么?艺术,作为人类最重要的精神产品,为何需要以金钱(拍卖会的成交价)为最重要的评价标准?随着新的科技不断出现,艺术必须依赖于高科技么?艺术等同于炫目的效果么?到底什么才是艺术最重要的部分?
曾经有一个展览对我影响很大。英国伦敦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(世界上最有名的几个博物馆之一)在2011年底举办了一个展览——“后现代主义:风格与颠覆,1970-1990”。在这个展览的前言中,策展人宣称,“在1970到1990年的20年间,后现代主义逐渐陷入了金钱的逻辑以及它本来想消除的影响之中”。这个观点意味着在在展览中宣告了后现代主义的结束。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发展走到了它最初目标的反面,与创立之初的对现代主义的否定和质疑的目标截然相反,艺术的逻辑变成了简单的金钱逻辑。
这个展览促使我想到一个问题:为什么在西方最重要的一个博物馆,会策划一个展览,表达这样一个观点:宣告过去数十年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的、最有一定的影响力的艺术潮流——后现代主义的“终结”?这不只是文化的危机,这是历史变局面前,全球在政治、经济所反映出来的全面危机在文化上的一个体现。
基督教、教都起源于犹太教,它们都是“一神教”,即认为世间只有一个创造及主宰世界的真神。一神教是带有典型的排它性,世间只有一个唯一的真神,没有其它的神,没有妥协的可能性(基督教内部的不同教派之间彼此视为异端、教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彼此不能容忍)。这就导致自诞生起,基督教文化和文化的冲突持续至今。基督教内部的几次分裂,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分裂,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分裂,也不能相互妥协,甚至以战争的方式解决(比如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“三十年战争”,形成了第一次全欧大战,伤亡惨重)。
一神教的思想逻辑上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“历史的终结论”。1989年夏,美国思想家弗朗西斯·福山在《国家利益》杂志上发表了《历史的终结?》一文,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是“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”和“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”(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真神,历史也将终结于我)。从“一神论”到“历史的终结论”,也必然导致“艺术的终结论”。美国美学家阿瑟·丹托1998年发表著作《艺术的终结之后》。“艺术的终结论”实质就是“艺术终结于我”,美式消费文化成为全世界艺术的样板,这也导致了今天全球当代艺术的状况。
艺术、宗教与哲学,都属于精神领域的最高层次。历史上,天主教的衰落,就在于教皇把自己从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领袖转变为封建领主,越来越注重争夺土地、财富和权力,而失去了自身最重要的价值。艺术,是一种精神产品,之所以保持重要的影响力,就在于它为人类带来精神上的活力、创造力、独立性和自我反思的能力。但当“当代艺术”越来越成为一种金钱符号,这也代表着它离自身的精神属性越来越远,同时,人们也不再相信艺术。
艺术的危机其实是全球的变化造成的,当世界经济格局发生转变,当美国不再对全球拥有绝对的优势,当美国不再愿意对世界承担更多的责任,当代艺术背后一整套结构和思维框架都慢慢的出现裂缝。“一神论”不再坚不可摧,“艺术的终结论”不再令人信服。艺术,作为人类最重要的精神产品,必须回到自身的价值。
这是历史巨变的时代,全世界格局和人类的未来都面对着从未有过的挑战。对当代艺术而言,陈旧的思维结构束缚了我们的创造力。重新思考西方,重新理解当代艺术,是在全球发生大的历史变局面前,思考我们怎么样共同面对新的挑战、问题和可能性。
艺术应该简单、直接、粗暴、直觉、本能、深入、惊骇、粗糙、不昂贵、不复杂、不精致、不优美、不讨好、不炫耀、不取悦、不完美、不舒服、不愉悦、不依赖、不妥协、不清新、不乖巧、不消耗巨大资源、不统治他人、不灯火辉煌、不歇斯底里、不扭捏作态、不琳琅满目、不黏黏糊糊、不唧唧歪歪、不干干净净、不整整齐齐、不故弄玄虚、不因循守旧、不循规蹈矩、不人云亦云、不盲目崇拜、不装腔作势、不摆出一幅资本家的姿态、不明明想着金钱却满嘴虚伪的谎言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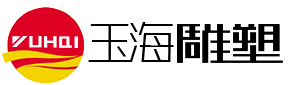

 相关推荐:
相关推荐:

